田野童话
已有 443 次阅读 2011-04-15 13:55田野有时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了教条。我亲眼在民俗学的研讨会上看到过教授们讨伐 “不田野者” 的不轨行径,那些可怜的文献学者们只好抱怨:“我们的文献研究路数好像很难被唯田野者们接受”。任何教条都会让我们产生一些偏执的想法和做法。比如,在阅读很多基于田野的学术著作的时候,最让我头疼的是文献综述部分的千篇一律。尤其是对古文献的综述上,好像大家都是在引用同样的史料,用同样的语气来解读这些史料。当然,这在只顾田野的人看来没什么,他们可能会说:“最有价值的是我的田野原创部分”。但是,学术终归是种对话,没有好的文献综述,那感觉便像是学者在自己的世界里去编织一个童话。
当然,忽略文献仅仅是问题之一,过分沉醉于田野的浪漫中甚至会让我们连一个童话都写不好、让我们疏于思考“如何把田野写下来”这个问题。我每年也要做田野调查,之前我有一个很自负的做法,总喜欢把随便压马路的经验也当成田野展示给别人。当然,广泛地讲,人生就是一场田野,写写短浅的见识,总是对写作有帮助,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当这种浪漫的幻想占据我的脑子的时候,我能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就不够了,写作的质量就大打折扣。这时,即使我去写作,也很难进入一种理性反思的状态去把田野写出来。
就像世上有读不完的书,世上也有着做不完的田野。就像一个人写作不可能总引用别人的文字,一个人也不可能总是沉浸在田野中而鼓捣不出思想。如果田野真的是学术的全部,那些职业旅行家们为什么不去做学者?同时,“以为调查过一两次就充专家” 这样的声音其实是种误解,批评的人一定是混淆了学术写作和游记的区别。好的学术作品其实能在有限的田野经历中讲出道理。
我所在的学校的田野调查课程分两段,修完要花一年的时间。第一段是一些基本的技能:采访、抄写、录音、整理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田野。第二段的“高级田野”,则将重点放在了笔头上:怎么将田野经历写好?这其中包括了临时的记录、阶段性的成形写作、以及对最终文体的文风改进(voicing)。这个过程就象是制作一张唱片,需要经历一个录小样,发EP,试听不同版本、最终定版、再到母盘master的过程。
Clifford Geertz在他的《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一书中论述过作者权威的问题,让人可以想象到学术著作的本质是树立这种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是需要用写作来炼造的。这点上,学者和小说家的意义是差不多的。学者也需要在笔头上画出图景的轮廓,雕琢一些细节,还需要整体的打磨。学者和小说家的唯一不同是,学者写的是他看到的田野,小说家带来的是想象中的田野。和小说家一样,学者完全可以在写作层面上发挥创造性,行文风格都十足地影响着表达的效果。在这个层面上,田野就成为了一个待加工的素材,谁能加工得有质量,谁就能有更多的读者。可惜的是,很多学生没有这种下笔头的行动力。
懒于写作,会耽误多少学生呢?纵然学术大师的接班人可以嘲笑媒体人的浮夸,但是一个事实却是,写东西的质量确实是有差别的。很多学生(包括我)写的文章质量不高的原因往往是田野带来的个人的想象太过强大,而忽略了写作作为社会对话的本质。换句话说,对田野的迷恋很容易让写作的人忘记了他的本职工作--为社会贡献文字。我有一次去录音,录出来的东西我反复和朋友说好听好听,意义非凡。不过,纵然我使用再多的感受性词汇去描述,朋友依然很难理解,并且对我说:“你说有意义那是因为你亲身经历过。” 至于怎么好,怎么有意义,则需要更多的笔下工夫去说明白。
现在,谈到田野,很多人都会问我:“你是不是要去大山里听村民唱歌啊”。我说,那样的事情旅游去做就好了。“其实我的田野是在一个可能你会觉得无聊的音乐机构里,但是我应该能把这无聊的经历写好”。我还会和朋友说,世界上有一种我很喜欢的学者:他们专心做田野,然后严谨地写田野;他们在不学无术的时候还到处旅游,会给你讲讲鸡飞狗跳的奇闻轶事,就像个普通游客一样,完全没有 “田野工作者” 的派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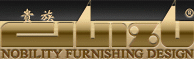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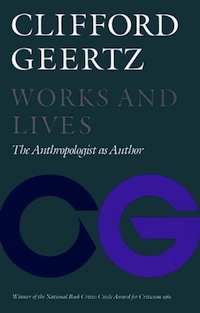





发表评论 评论 (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