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田牵着山寨
热2已有 476 次阅读 2010-10-16 12:55大闹山的苗寨的早晨
大顺苗寨
亚净 和 师范大学的同学
拍照
吃午餐罗
无空又被敬酒了,当团长享福啊!哈哈
虫虫在写游记
出寨子收割糯米去罗!
老K很也专业啊
当当一学就会收割糯米了
苗族女孩在捆剪好的糯米
很漂亮的MM
无空童鞋 和代老师 合影
瞧这堆人,都不闲着。呵呵
无空 挑糯米很专业了
老K也很酷!
远望大顺小学
师大的童鞋们
别离时刻
再见,大闹山苗寨
另外给大家转一篇很美的散文,《梯田牵着山寨》。
作者:吴鹏毅(侗族)
(原载《民族文学》,2005年第4期)
傍晚。那一层层连延蠕动的梯田,在苍劲的山风里,从远古的背影中走来,情意绵绵地盘结在大山腰,层层跌荡,从坎里延伸出来,逶迤潜行,又弓着腰,爬进另一道坎里。爬着爬着,就爬满了一片山坡。
高高地踮起脚跟,从远处嘹望那爬着潜走的梯田。只见梯田一层一层的,逐级而下,从山顶也是爬着的黛灰色的山寨的脚下一环一环的盘结到山脚,就像是山寨中木楼旁的那些防火水塘中微风撩起的层层涟漪,那么的轻柔、细微;又好像是由山寨中间,
那高高耸起的鼓楼中“咚——咚——咚”的鼓声向地表发出阵阵声波一样,层层地泛开传播而来,很是壮观。
不知怎么的,艳觉得那梯田、那水波、那鼓声,总是能让她觉得舒坦、惬意,而同时又有一阵阵的振奋。
在一弯细细地田坝基上,一头老牛,沉着的朝前走,后面跟着的艳的爷爷,背上挎着犁耙,手扬赶鞭,神情凝重的在缓慢跟随。爷爷时不时的引吭吆喝,吆喝声和着牛铃的叮当声,此起彼伏,合奏出那一首永远也唱不完的乡谣。歌声穿越浑黄的长空,击透了岁月的帷幔,不紧不慢,不沉不激,悠悠然地响切于大山深处……
天边,一轮红日,正在从日子的肩头上,跳宕着跌落,砸下去,砸下去,溅起了漫天的红霞。既而,又重重地涂抹在大山的肌肤上,贪婪的亲吻着大地。
于是,大地,红了;山,红了;山寨,红了;梯田也羞得,红了。
艳在如血的残阳中,数落着牛蹄的响声。数着数着,就懵了。因为,那牛蹄踏落后,有的就立刻蒸发掉了。蒸发掉了的牛蹄声顷刻间淹没在大山的褶皱里,淹没在阿公那双温和而又深邃的眼神中,淹没在梯田那春夏秋冬的轮回与变换的时空之中……
“瞧,阿公,这田坝上留着的一个个牛蹄窝,到底是往前走的还是往后走的呀?”艳不只一次的这样问她爷爷,“是前蹄的吗?还是后踢呀?阿公,这牛好象是横着走吃草呢”。
公艳每一次都只是微微的一笑,“傻丫头”。
艳每每这个时候,就会凑近去仔细地看着,牛蹄窝或深或浅,或圆或缺,都聚着一洞的雨水,象是一个个睁着的水汪汪的眼睛,在仰望天穹。艳看到,她自己的小脸出现在水里,还隐隐约约地不时的闪现出阿公脸庞上的皱纹。更奇怪的是,似乎还能扑抓到她家那头老牛浓重呼吸的声浪,以及爷爷和爷爷的爷爷们那丰收的喜悦神色。
艳喜欢吃糯米饭,特别是花花绿绿样的五色饭。所以,就经常盼望过牛节。
每当农历四月初八一到,山寨里的人们就要过“牛神节”。这一天,人们给牛象征性的披上一件蓑衣,让牛好好的在家休息,并拿鸡、鸭、鱼等一些祭品,摆在牛栏边,敬贡牛神。以特制的五色糯米饭敬献,表示对牛辛勤劳动的深深谢意。同时,又在默默地祈求着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每一年的这一天,公艳都要到山寨坡头的那块“公田”边,摆上神位,贡上酒水和三牲祭品;接着,一些老人和一部分壮年人,就各站成两排等候着;然后,公艳把犁耙、锄头等几件农具摆在神坛前,再焚纸烧香;之后,公艳手持三炷香北向,面朝“公田”跪拜,口中还念念有词的唱着那首古老的祭词:
“各路神灵来吃酒/世人祈求你保佑/保佑田中禾谷壮/保佑我屋丰收年/正月阳雀叫过/二月雷婆鸣天/三月耙山动土/四月谷雨下秧/五月扯秧插田/山上种旱谷/田里栽水稻/山谷收成好/田谷收获多/山谷茂盛如牛尾/田谷茂盛如马鬃”
艳知道,这是一块“滚泥田”。爷爷总是不让艳去参加这个活动,说是女孩子不能参加这样“谨重”的事。
但每一次,艳都是躲在不远处,偷偷的看着阿公他们,看着那些老人、大人、和那些男孩子们。甚至,还看着一些男孩子扒光了衣服在做“滚泥田”。听阿公说,“滚泥田”是山寨中人们一个特别庄重的活动,男孩子长到五岁、十岁、十五岁这三个年龄的时候,就会带着个自不同的期盼和美好的向往,三次滚过这块水田。说是一旦滚过一次,人就更加健壮,更加聪明。
艳从小就很向往着健壮,也很想到“公田”里跟男孩子一样去“滚泥田”,可是阿公他们怎么都不答应,说不能坏了规矩。尽管这样,艳心中这种强烈的心火,一时也没有熄灭过。事实上,艳长得确实的“健壮”。是健壮的美。
艳如今已经是大姑娘了。
听——牛蹄劳作时的响声,依然的那么响亮,依然的那么清脆。牛蹄声浪如云雾般的缭绕在层层梯田之间,缠绵在梯田和山寨连着的那一座大山之中……
天,渐渐地暗下来。
公艳正挎耙戴笠的,从田埂道间轻轻地走过。艳和她的几个同伴们,嘻嘻哈哈的飘然荡过。而憨憨地梯田,似乎也正怀抱着丰收,在陶醉。
不料,一阵山风吹来,把稻谷的芳香和女孩们的笑声一股脑儿都偷跑了,丢撒得到处都是……
夜 风
夜里。
风儿倒挂在木楼外的树枝上,在绿叶和枝丫间撒野似的狂舞着,摆弄着她那三寸金莲四寸腰。
木楼看不惯山风,不买她的帐,架开庞大的身躯,拉开四四方方的脸,肃然的挡住山风:“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风儿被拦截,发出呼呼怪叫,俨然谁家一个小儿尿床挨揍的不顺畅的哭喊。
艳说她这几天,心里空得很,没谱。她说,想出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但是,左想右想,总觉得不是办法:一是阿妈放不下心,二是自己也害怕。怕弄得不好,被人家骗了,卖到哪里去做别人的小媳妇,那就永远不能回来了,永远也见不到阿妈了。可是,整天呆在家里也烦。
艳自从那一次从城里回来,就再也没有出过山寨一步。那还是在刚去区卫校读书时,一天,艳打电话回来,跟阿妈说:“妈,我想家”,然后,就泣不成声。阿妈听了之后,心里也像是被刀割了一样的痛。
第二天,阿妈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就糊里糊涂的,去把艳接了回来。
回来的那天晚上,艳在火堂屋里坐着,阿妈觉得塌实多了,艳自己也觉得温和,不怕,也不累。
就这样,艳在卫校呆着前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那是艳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
吊脚楼的吊柱,偏厦盖着的杉树皮尖、偏厦伸出的压扛条,都绊住了风的腿,扯住了风的衣裙,牵住了风的长发,让后面的风跟不上前面的风。风儿,狂叫着、撕扯着、喊得满天漫地都是风声。
风儿不甘示弱,像是故意跟山寨过不去似的。风撕开她那哇哇乱叫的嘴巴,不要命似的猛吹风,从寨东头吹到寨西头,再从寨北边刨向寨南边。狂刮着鼓楼顶上的葫芦串,恨不得把葫芦串刮得脱皮,刮得烂坠;狠吹寨尾的风雨桥,吹得阁楼里神龛上的佛像更加的暴牙裂齿,更加的竖发暴眼珠;狠吹那村头的寨门,吹得寨门哑哑欲倒。
艳说,过了这鬼节,我想出去打工。去沿海,听说,那儿,很容易捞钱。他不想那么快就嫁人,她说过女孩一长大就要嫁人,一嫁人就得当妈,那样多容易哀老呀。
可是,一到天黑,寨里的后生们就抱着琵琶,在她家的木楼下,叮叮咚咚的弹唱着情歌,喊阿艳开门来“坐夜”谈情,听——
太阳太辣我也想
大雨滂沱我也思
寨里妹多我不爱
不知为何单想你
艳外出打工的想法没有变成现实。这似乎成为她心中一个永恒的梦。
阿妈说,艳长得好,生得嫩,在外容易坏事。阿妈还私底下拿寨尾的阿芳来作例子:人家阿芳还没你长得标,出去不到一年,就打(胎)了两次;家人都没跟说一声,就跟人跑了;说是吃穿不愁。是陪吃,又陪喝。
后来,又有一个亲戚介绍,要艳到县里的宾馆去做礼仪小姐,去坐台。说是别让浪费了艳的身段和容貌。
艳没有去。她说她疼娘,也恋家。
但是,不知怎么的,艳说她还是成天的在想入非非。她想,同伴们都嫁了人,有的都当了娘。瞧她们整天忙不完的活,弄得一个个不像人样的脏,不像人样的乱。一个女人就这样嫁了人,当了娘,再像阿奶一样做了太婆,然后老去,入土,一辈子就这么个样了。可是…… 可是外面的世界一定很好玩,很精彩的呀。于是,艳就一天到晚,望着屋对面的那座大山,任由自己的心和思绪在飘、在甩,飘着甩着就游到了大山外的那个天底儿去了。
木楼廊处,竹竿上的尿布,被风挑起,在夜空中翻飞。榫头上挂着的鸟笼,遮蓬布被半掀而起,在屋檐下翻转。
山风还没有尽兴,更加的凶煞起来,专门找着木楼的厢墙,钻进木板的眼孔,灌到屋子里到处搜寻,到处乱撞。墙上被烟熏得昏黄的年画,被风搅得上下左右的不停晃荡;那被小孩子撕开一大块肚皮的门神,这时仍旧在虎视眈眈的与乱风对峙,但似乎又奈何不了风,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着一种十足的“神气”,在与山风撕打、抗衡。
再后来听说艳因为又要去读书,而被阿爸数落了一顿:
“当初不想读,跑了回来,现在又要读,想七想八的,学什么名堂!全村就你一个女孩子读书。你看看山崽,他还是省城里读的,现在还不是蒙在家里,没事干,在待业呀!识相点吧你”。
艳关死房门,蒙在被窝里闷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这一下可把阿妈急坏了,担心艳想不开,生邪念。于是就哭着叫着要艳开门:
“宝贝女儿呀,你开门呐,娘没有怪你啊……”。幸好她疼娘,娘叫她,她也应,就是不开门。
第三天早上,艳终于开了房门。一头乱发,托着两个鼓鼓而润黑的眼圈,瘪着个小嘴,半笑不笑的对阿妈说:
“妈,我饿……”,就直奔火堂角落里的老橱柜……
从那次以后,艳再没有提出要出远门,再也没有提出要去读书,而是跟着一伙同龄的姑娘一起,进入山寨里一个宝石加工作坊。她们把那些宝石磨成半成品,然后,由老板拿到城里去卖给大老板。姑娘们一天可以磨制出一二十块钱,熟手的一天可以挣到二三十元,甚至还多。
她阿妈说,姑娘们整天堆在一起,有说有笑的,轻轻松松,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愁,而且还捞到钱。
这也好。
确实,姑娘们既挣到了钱,又找到了她们的乐趣,找到了属于她们的生活天地。
木楼底下,刚才姑娘和后生们捶布时砸了满屋的木槌声,被风吹散,山果一样的撒满一地。火堂里久久回荡着的“坐夜”时泻出的绵绵情思细语,被风搅得缠缠绵绵;顷刻间,从厅堂院廊的长窗一骨碌儿,全被漫到木楼外,散在石巷过道间,混合在弥漫着的夜里谁家炒菜时的飘出的酸肉香,然后被夜风一起拖着走。一刹那,不知全被带到哪儿去了。
夜空中的山寨,静静地伏在那里,睡得正香。
山风,也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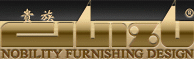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唉,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