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逃生”十二年
已有 836 次阅读 2011-04-29 16:22在这个穷困而执著的庄稼汉看来,这并非一个宿命意义上的黑色幽默,而是赤裸裸的精神和现实的双重夹迫。为摆脱“无后”的耻辱和躲避可以预见的制裁,袁铁明领着妻女躲进深山,在一个山洞里与世隔绝生活了12年。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性别赌局”中,袁铁明不断被边缘和遗忘,又企图以不断生育来自救。在梦想破灭的2010年,走投无路的他将最小的女儿送人,尔后被警方发现。袁被迫走出丛林,回到早已面目全非的现代世界。
在山的深处,袁铁明一家在淤塞的山洞中安了家。他们开荒种地,挖井取水,成了村里人眼里的“野人”。 (骆晓强/图)
“没有男娃头抬不起”
在回程的公共汽车上,袁铁明对妻子宣布了刚刚做下的决定:“我们逃外面去,一定要把男娃生下来。”
2011年4月23日下午,44岁的袁铁明在一块新开垦的坡田边挥舞着刚磨好的镰刀。动作还算麻利,他却感觉自己有些老了,心力也大不如前,就连年轻时一些志在必得的事情也慢慢变得模糊——例如想象和儿子在田间挥汗如雨,然后看着他长成一个强壮的男人。
如今这一切已遥不可及。过去12年间,除了不断增多的女儿,袁铁明几乎毫无作为。长期焦虑、辛劳和毫无节制的生育,更严重损害了他和妻子的健康。“这就是命。”袁铁明叹息。
位于河南省西部的嵩县风光如画,却极为贫困。袁铁明的家就坐落在县城西北四十多公里外的深山里,所有建筑物是一个废弃的山洞,两间看得见天空的草棚和一个用枯枝围成的简易厕所。在这里,袁铁明很努力地种玉米和放羊,但仍不能填饱6个女儿的辘辘饥肠。这一切在他看来,仅仅因为是“少了一个儿子”。
袁铁明出生在16公里外的小章村,只上过半年小学。由于大哥年少夭折和弟弟过早出门谋生,他成了祖业的实际继承人。一座5间房的宅院和两亩地让日子过得还算凑合,但问题也随之出现:1999年,妻子谢娥为他诞下了第二个女婴。
对一个中国农民来说,这意味着合法生育权的终止,但对有着强烈的家族使命感的袁铁明来说,则又是另一回事。“农村人,要的就是根脉。”他说,“没有男娃连头都抬不起。”
这是中国农村不言而喻的现实。纵使在21世纪的今天,儿子仍被农民视作赖以炫耀的财富和勋章。
袁铁明的话在自己身上得到应验。他为人直率,易得罪人,“无儿”自然成为记仇者反击的把柄。“他们故意在我面前说些难听的话,斜着眼看我,好像我有多可怜。”袁铁明说,“连母亲也要跟着遭罪。”
办法也不是没有。一些同样盼着延续血脉的邻居会偷偷多生一胎,到时交些罚款就行了。但袁铁明没有钱,他和妻子都不识字,每年那点收成还不够换一身体面的衣裳。所以当1999年8月23日计生人员上门要将袁氏夫妇拉到县城做结扎时,他感到毁灭性的恐惧,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后来(谢娥)验出血压高,手术做不了。”在回程的公共汽车上,袁铁明对妻子宣布了刚刚做下的决定:“我们逃外面去,一定要把男娃生下来。”
夫妻俩马上回家接上两个女儿,连大门都不关就跳上了一辆城镇公交。傍晚时分他们到了一个叫小滚沟的村子,一个三面环山的长条形村庄。
袁铁明一家沿着山梁往村后的无人区跋涉。到了一个开阔的斜坡时,妻子和女儿实在累得走不动了。袁铁明发现了一个淤塞的山洞,用手掏空,和家人开始了第一个不眠之夜。
山里的风大得惊人,还夹杂着野兽凄厉的叫声。被疲乏和恐惧袭扰了大半夜后,大女儿金巧终于颤抖着哭起来。袁铁明训斥道:“不许哭,有了弟弟才回家。”
袁铁明决定不再生了。“吃不消,也养不活。”他说,“女儿也不赖,日子慢慢过,会好的。” (骆晓强/图)
“又是一个女娃”
几个月后,袁铁明在失落中偷偷回了一次老家。亲戚们对他的出现喜出望外,同时也告诉他一个坏消息——由于非法生育和出逃,村里已注销了他一家的户口。
袁铁明决定留下来,并为未来的儿子打造一个新家。
他开荒种地,挖井取水,还用木桩和藤条编了篱笆和床。妻子和孩子们则光着脚去摘浆果和打柴草。玉米糊和红薯是最常见的食物,吃完了还可以挖一种叫“格兰叶”的野菜。后来,一只羊羔加入了这个破败的家庭,增添了几分生气。
危险也无处不在。野狗是最讨厌的常客,它们成群结队,盯着孩子和羊。袁铁明于是到哪都把女儿绑在身上。妻子谢娥温顺坚强,但也难忍这里凶猛的蚊虫和毒蛇。“天一黑就胆颤心惊。”她说。
但最无常的还是自然力量。一次连夜暴雨,洞口禁不住浸泡突然倒塌,泥石流向洞内涌来。谢娥和丈夫抱着孩子强行冲出去,蹲在玉米地里淋了一夜。
羊倌老李头第一次见到衣衫褴褛的袁铁明时竟不敢上前。“都不成人样了,怕是犯了啥事吧。”后来听了这个男人的故事后,他激动得抱着面条就往山上跑。“都是庄稼人,看着揪心。”
袁氏夫妇的事逐渐在村子里流传开来。或出于好奇,或出于同情,一些村民开始零零星星地往山上送东西,帮助他们脱离原始社会。于是,袁铁明一家有了鞋、毛衣、被褥和一间铺着塑料布的窝棚。家像样了,更值得欣喜的是——谢娥又怀孕了。
这是进山后的第一个春天,回家的愿望已被积攒得如此强烈,袁铁明一心认定这肯定是个男孩。他张罗着为妻子补充营养,但不过是稠了点的玉米糊、自调的草药汤和好心人送来的奶糖。
度过满怀希望的盛夏和初秋,终于等来了谢娥临盆。在那个忐忑不安的夜晚,袁铁明准备了剪刀、碘酒、热水和煤油灯——他要自己接生。“我们没钱上医院。”
这无疑是一次荒唐的冒险。由于毫无专业技术和卫生条件,谢娥会随时死于任何一次再轻微不过的失血或感染。那一晚,如豆的灯光下,袁铁明小心挤压着妻子的腹部,谢娥撕心裂肺般的喊叫声回荡于整个山谷。
一个小时后,筋疲力尽的袁铁明抱着一个全身血污的婴儿,颤抖着剪断脐带。像要揭开潘多拉之盒,袁将孩子缓缓举起,却看见一个不愿相信的事实——又是一个女娃。
几个月后,袁铁明在失落中偷偷回了一次老家。亲戚们对他的出现喜出望外,同时也告诉他一个坏消息——由于非法生育和出逃,村里已注销了他一家的户口。
“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让统计数字更漂亮些。”一位基层干部说,“它们往往脱离实际。”
袁铁明失去了公民身份,同时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保障和权利。后来,小滚沟一带的村民半开玩笑地称他为“野人”。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描述他的生活状态,二是描述他的身份特征。“黑户”袁铁明放下了最后的顾虑,回到深山里继续等待“儿子”。
“养不起了,送人吧”
第六胎寄托了袁铁明最后的期望。接生的那天晚上,他在地里烧了一炷香,祈求上天保佑,但现实仍残酷地给予他最后一击——还是女孩。
袁铁明在荒山里迎来了新世纪。他命运的赌局还在继续,但结果令人沮丧——2005年和2007年,谢娥又诞下老四袁莹和老五袁丽。
山上日复一日,山下却急遽变化。一些超出袁铁明经验范围的东西悄然涌入,电视、冰箱、手机、电脑乃至互联网,它们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还有思想。
山下的村子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缩影。这个庞然大物总是雄心勃勃,善于创造奇迹,但也有少数问题令她感到棘手,例如人口。
计划生育30年,中国人口又站在了十字路口。发展失衡危机已经取代高增长压力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性别结构失衡又是外界热衷讨论的焦点。
据权威资料推算,到2020年,中国男人的数量将比女人多出近3000万,危害之深远,不亚于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而生孩子的人永远不会如此高屋建瓴,中国人的生育热情仍居高不下,并逐渐以富人阶层和偏远农村为主力。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人口哑铃最沉重的两端。
“在基层,上级政策和实际往往是脱节的。”一位服务乡镇14年的计生干部说,“为应对各种不现实的指标和任务,很多工作最后都变成了数字游戏。”
因此,即使作为一名情节严重的“超生者”和“藏匿者”,“黑户”袁铁明不会被纳入任何的统计数据。他在这样的政策夹缝中平静地迎来了2010年。这一年,他的妻子第六次怀孕。
袁铁明的心情很复杂,他觉得自己没有强大到能连续接受六次失望。他下山找了一位长辈,对方告诉他一个古老的传说——如果前面都是女的,那第六胎一定会是男的。
袁铁明很高兴,干活也更加卖力,还顶着烈日到山崖上挖草药。有零钱了就到集市换几颗奶糖给妻子“进补”,但谢娥却把奶糖用嘴啃碎分给孩子们。
年近四十的谢娥身体越来越差,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由于每次产后都缺乏营养和过于辛劳,高血压和关节炎频繁折磨着她,头发也过早地花白。
第六胎寄托了袁铁明最后的期望。接生的那天晚上,他在地里烧了一炷香,祈求上天保佑,但现实仍残酷地给予他最后一击——还是女孩。
12年的等待和付出就这样无声终结。谢娥虚弱地哭了起来。袁铁明则静静地帮孩子洗好身体,包在一件旧单衣里,说:“养不起了,送人吧。”
玉米糊和红薯是最常见的食物,吃完了还可以挖一种叫“格兰叶”的野菜。 (骆晓强/图)
“拐卖你女儿?”
袁铁明接到派出所电话叫他去一趟,赶到时才知道自己已成了“拐卖儿童嫌疑人”。袁问拐卖谁了,对方回答:“你女儿”。
老六甚至还没有名字,就要离开这个家。除了袁铁明自己,没有人能理解。
袁铁明迎来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而他最终选择了现实。“实在没有多余的粮食了。”他说,“我不能看着她饿死。”后来,一个远房亲戚表示愿意收养,并表示付18000元的营养费。谢娥勉强答应。
5天后,收养的人上门了。袁铁明往襁褓中塞了糖和香蕉。谢娥泪水涟涟,对丈夫说:“你这是剜我身上的肉啊。”袁铁明感同身受,但一直忍到深夜,他才在被窝里放开泪腺。
梦破后的袁铁明在女儿的眼中变得更像一位父亲。他开始给她们做玩具——被剥去树皮的树枝和形态各异的木块;或者在傍晚带她们上山梁,迎着狂风奔跑;天气好的时候,他还会把女儿们领到树林中,尝各种植物的味道。
鉴于妻子每况愈下的健康,袁铁明决定不再生了。“吃不消,也养不活。”他说,“女儿也不赖,日子慢慢过,会好的。”
日子在平静中溜到2011年3月4日,送走老六后约一年。袁铁明接到派出所电话叫他去一趟,赶到时才知道自己已成了“拐卖儿童嫌疑人”。袁问拐卖谁了,对方回答:“你女儿”。
警察告诉袁铁明,有人举报他将女儿送人并收了钱,而且事实清楚,应以拐卖儿童罪论处。袁铁明辩解无效后被拘留。7天后,妻子谢娥七拼八凑了3000元才将其取保候审。
袁铁明觉得事儿闹大了,到处托人找关系、问对策。一个亲戚给他介绍了律师,律师看过袁的材料后反而对他的藏匿经历更感兴趣,于是发帖到“嵩县贴吧”。这是当地一个颇具独立精神的民意汇聚地,很快,人们有了反应。
几天后,一行志愿者到山里探望袁铁明。这是封闭与现代两个世界的碰撞和交汇,前者惊讶于后者的原始和艰辛,山洞、窝棚、煤油灯都让人恍如隔世;而后者则感叹于前者的神奇,一种按了就“立即”看到自己的相机,一种带“电”的“脑”,就像看科幻片。
一个志愿者在考察笔记里写下当时的心情——我无法形容这样的房子,我几乎不相信这是21世纪的中国。
袁铁明充满传奇的经历通过互联网被进一步放大,人们因同情而关心他的命运。他的“拐卖儿童案”成了最热烈的话题。当“嫌疑犯”袁铁明还在他的草棚里感叹投诉无门的时候,互联网已经通过它的舆论能量影响案件的审理过程——传唤袁铁明一个月后,嵩县公安局向网民发布了案件情况说明,引发公开讨论潮。
“会有新家的”
为消除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当地正努力进行淡化处理:一是恢复袁铁明一家的户口;二是防止他接触外人,尤其是记者;三是谨慎处理他的案件。
4月的一天,为询问案件的进展,袁铁明穿上那条最好的蓝色呢子长裤和绿色干部装进县城,下了车才发现城里早就不这样穿了。
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12年前,那时候没什么交通灯,街道也很安静,人们还热衷于骑自行车。而现在,年轻人夸张的发型和街头广告都够他端详半天。人们在他身边来来往往,但没有能想到眼前这个男人,直接从1999年来到了2011年。
在热心志愿者的帮助下,袁铁明带着妻女下了山,住进村子里一处空置的宅院。出于习惯,临走前他仍将庇护了他12年的山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山下的生活要更热闹,袁铁明需要重新学习,例如如何和邻居相处,如何察言观色,如何了解更多的热门话题……
下山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卖掉两只羊,抱回一个电视机。较之12年前,电视节目的丰富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很快,他爱上看新闻,妻子喜欢看电视剧,女儿们则抢着看动画片。
前些天,一个亲戚送给他一台旧手机,这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按几个键就能把人找着了。”袁铁明说,“放以前得跑多少路呀?”
“小小拍客”是最先关注袁铁明的一位“公民记者”,也是积极帮助他回归社会的志愿者。他将袁铁明一家的视频放在个人新闻博客上,希望聚集更多的公益力量来扶持这个被遗忘的家庭。
“他的想法和逻辑必须放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来理解。”“小小拍客”说,“他被注销了户口,被社会抛弃,缺乏温暖,因无力改变现实而作出这样的选择。”
为消除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当地正努力进行淡化处理:一是恢复袁铁明一家的户口;二是防止他接触外人,尤其是记者;三是谨慎处理他的案件。
现在,袁铁明所在的小滚沟是一个绷紧了神经的村庄。村干部在村头蹲点,看见陌生面孔就通知袁铁明上山躲避。这种人为的真空增加了他的不安感,他很穷,还背着官司,他需要帮助和咨询,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适应新的生活。
4月18日,袁铁明带着妻子谢娥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小章村,领回被中断了10年的户口。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能与过去续接,村子变了样,年轻一辈的都已不认识了,祖屋也倒掉了,家具衣物都腐朽成淤泥滋养着疯长的杂草。
站在这个空荡阴森的院落,谢娥仰头对丈夫说:“家没了。”袁铁明打量着周遭,说:“会有新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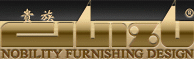









发表评论 评论 (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