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版《奋斗》:《山里的男人》
热2已有 1212 次阅读 2011-04-14 10:51前言
很久以前,我就在思考,走出农村的人们,将走向何方。这是个很深沉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村人离开土地,离开自己的家园,像洪水一般涌进城市,但城市似乎并不打算接纳他们。运气好,也许他们能够在城市里“混”出个生活,但付出的代价一定是城市人的许多倍。可是,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并不如意。他们想在城市的土壤里播种梦想,却发现,钢精水泥铺就的街道,并没有他们可以扎根的沃土。而当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农村,却发现,曾经的良田已经一片荒芜。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但农村人自己却很少去思考。他们在外拼搏,也许有一天真的有望“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也许依旧“一无所有,空手而回”,甚至得不偿失,荒废了青春甚至失去了生命……但不管结果如何,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否都一样一片空白?城市能够孕育梦想,农村为什么就不能呢?
《山里的男人》是我对农村思考的结果,也许它有些拙劣,有些肤浅,有些残缺;但无可否认的是,我真的思考过,现在还在思考,未来也还继续思考……我想要表述的,不只是故事,而是我对生命的思索,对灵魂世界的追寻。
我想通过一个农村青年的奋斗历程,来展现新时代农村人应该具备的精神面貌,他们对自身命运的认知,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对爱恨情仇的选择。
这一切的思考,也许只是因为,我也是“山里的男人”。
第一章 缺了一条腿
1
我听说杨少平前两天已经从城里打工回来了,还带来了一条瘸腿。村头巷尾人们已经当香饽饽一样议论着这件事,唯独我还没见到他的人。自从出去打工那天算起,这小子,已经有四年没回家过年了,平时一个字也不往家里捎,好像早就忘了山里还有个家,还有生他养他的爹娘。
我们山里把过年过节家人团圆看得比什么都重,有些人到外面闯荡一年,到头来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但还是想方设法借钱甚至一路乞讨赶在年前回来了。回到家里,非但没有遭骂,欠的钱家人还得东凑西凑替还上了。大家都信奉那样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见了平安回来的人,往日的气话怨言,就像见了太阳的晨雾,立刻烟消云散了。我们这里,去城里打工常年不回家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还在坐牢的王秃子,一个是死在外边的吴金贵。他们不回家是情有可原,而他杨少安不回家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他家里人逢年过节也没少叨念他,只是各有各的态度:老父亲骂他忘了祖宗,连畜牲都比不上;哥哥嫂嫂说他心里没个“孝”字,一个人在外面畅快,撂下父母不闻不问;最受罪的是老母亲,逢年过节都少不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人倾诉对儿子的挂念。儿行千里母牵挂,牵挂的又何止做母亲的呢?
现在,新年早过,年关尚远的时候,杨少平却大张旗鼓地回来了,也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况且还带来了一条瘸腿。
这阵子我正为鱼塘加坝忙死忙活,以防即将到来的雨季。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没来得及去找他讨根烟抽,杨少平却先找上门来了。他来的时候,我正在河里捡石头往岸上抛。这小子,还是和以前一样,远远的就拉开了嗓门。
“大成,你个卵崽,自立门户了?”他一边喊一边朝我走来,一瘸一拐的,“月亮都快上来了,把大叔一个人撂家里,鱼塘当家了不是?”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拍拍手上的泥灰,走上了岸,有些意想不到,“我正愁着没烟抽呢。”
“我家里去找你了,叔说你还在河边。”他一边说一边从胸口的衣兜里往外掏烟盒子,“我问叔河边什么地方。他说鱼塘,我就来了。我听说你承包了这十亩鱼塘。”
“我看这鱼塘荒废着怪可惜的就承包下来了。”我说着已经接过他递来的烟点着了,“你成大老板了,抽中华,一根顶我们老农一天的工钱呢。”
“嘿,剩半条贱命回来已经是祖宗保佑了,还老板呢。”他嘴边抿出一丝苦笑。
“你还记得祖宗呢,我以为你早就换了祖宗呢。”听他嘴里蹦出“祖宗”这两个字,我就犯起了数落他一下的念头。
“你小子就不忘拿我寻开心。”他不愠不怒,拿白眼瞪了我一下,“听说这两年赚了不少,是个人物了你。”
“拿身体血汗当本钱,挣几个酒烟钱。”我说,“说不上赚。”
“对我你还口严,别欺负我初来咋到啊,我可都听说了。”他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乡亲们现今一开口可都先提到你潘大成响当当的大字。”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我打量了一下他的腿,“怎么回事儿?”
他眉头立刻微微皱了起来,现出难看的一脸表情,对着天边深深地吐了一口烟,送出一句:“一言难尽。”
“想不想尝尝没有吃过饲料的鱼?”看他很是难过的样子,我也不好再追问下去。
“不想吃我来找你做什么?”就像瞬息万变的天,他立刻又浮起了满脸奸邪的笑意,“网两条来尝尝鲜,说真的,几年没吃过咱们这里的鱼了。”
我网了两条斧头板大小的鲤鱼,问他:“够了没有?”
他笑了笑说:“我又不是饥民,你还真当我是讨饭的?”
晚上我把对面的蒋松爷也叫来了,加上我爸,四个人也没把两条鱼吃完,倒把家里剩的半瓮米酒喝个精光。杨少平向来不胜酒力,几年不见,其他的地方好像都变了,唯独这项没一点变化。站起来他已经摇摇欲坠了,嘴里含混不清地骂着什么。出门的时候,他坚持说自己没事,但两位老人还是不放心他一个人走路,叫我把他送回家。我把他送进门后,才折回了鱼塘的小屋。
外面是洗过一样清澈的月光,洒落在四周静谧的田野上。和月光一样清澈的,是我没有一点睡意的眼睛。我走出了小屋,坐在坝上抽起了烟来。远处的秧苗正在抽长,在晚风的吹拂中翻滚着,阵阵草香沁人心脾。但让我无法入睡的,不是月光,也不是草香,而是杨少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那只跛脚。
2
我和杨少平同一年出生一起长大的,但并非从小就是好朋友。和其他孩子一样,那时候他也从心里瞧不起我,一样骂我是没妈的野孩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初中。初中毕业前夕,杨少平和镇上的学生发生了矛盾,被几个人拿着棍棒围攻,在场的没一个肯出手相救,就是平日称兄道弟的那帮人这时候也做了缩头乌龟远而避之。眼看那帮人的乱棍就要劈头盖脸落下的时候,我冲进食堂厨房抓了一把菜刀冲了过去。见到我手里明晃晃的菜刀,那帮镇上学生退却了。杨少平得救了,但我和他不得不离开了学校。从此,他把我当成了救命恩人,欠了我的人情。每次提起这件事,他都觉得很愧疚,说他毁了我的前程。因为那时候我在班上的成绩名列前茅,老师觉得我有望考得了高中,将来可能还上大学。但为了他,一切都成了泡影。我告诉他,初中三年已经让我家里不堪重负了,我从来没指望上什么高中,更别说大学了。但他还是不停地摇着头,唉声叹气地重复一句话:“你救了我,我却害了你。”
我告诉他,相比于上什么高中什么大学,朋友对我来说更重要。那些东西太遥远了。我从小到大没有过一个朋友,无心树敌,把我当敌人的却一大堆。他很负疚以前对我那样坏,发誓以后一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我。为了让我相信他的话,他把自己的指头咬坡,在村外的石头上写下了“兄弟”两个血字。虽然那两个字早被风雨吹刷干净了,但每次路过的时候,我总情不自禁地停下来。想起夕阳下两个少年信誓旦旦称兄道弟的样子,心里就像装满了春风。
从学校出来后,我们又在家里度过了空虚的两年,然后结伴下广东打工去了。我去了两年,受够了城里的气,就不再去了。而他坚持只身南下,誓言闯出一片天来。谁想到四年后再见,他的豪言壮语已经化作一道抹不去的伤疤。
杨少平瘸腿的事,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揣摩着答案。有人说,他是跟人打架被打断的,有人说他是出了车祸,有人说他是欠赌债被人敲断的……人们凭着自己力所能及的想象,各衷一是。而他本人在家人的追问下,说是在工地上摔断的。我既不苟同人们毫无根据的猜测,也不相信他跟家人说了实话,但我也没打算问他。既然他不说,就一定有他的原因。被人逼迫说出自己不愿意透露的隐情,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我很久以前就尝试过了。一个人,没有经历过你经历过的那种痛苦,就算他口口声声对你说他能理解,也不能体味到万分之一。所以历来我都没有刨根问底的习惯,因为我也一直逃避着被人刨根问底的目光。
杨少平闲在家里也不知道干什么,就来鱼塘帮我的活。说实在的,他垒石头的水平比我高,可能这有遗传因素。他祖上曾是有名的石匝,他的爸爸和哥哥都是垒石头的好手。我们村子里谁家起新房开房坪,都喜欢请他们父子俩。
“想不到一回来就成名人了。”杨少平几分无奈伴着几分自嘲地说,“可惜巴掌大的地方,要在城市里,就该上报上电视了。”
“出名是好事啊,有人拿钱还买不来呢。”我跟他开玩笑。
“人怕出名猪怕壮,吃完说不完啊。”他先叹着气,旋即嘴边却露出了满不在乎的笑意,“就让他们说去吧,那嘴巴闲着也是闲着,*不撒尿,还留着当大炮?封闭了几百年,也该松松了。咱们这地方的山多得跟城里的房子一样,活了一辈子就看到个巴掌大的天,还能指望怎么样?”
“听你这么一说,到城市里逛了几年,回来还真瞧不起咱们这山里人啰?”我半认真半玩笑,“先前你爸说你忘了祖宗我还替你不平,现在看来活该。”
“瞧不起我还回来个卵?”他不焦不躁地笑了起来,“说句实在话,想来想去还是咱这里的人好,穷是穷了点,可活得自在,空气都新鲜,不像城市里。书本上说的‘青山绿水’指的就是咱这地方,你说是不是?”
“我可不记得书上说什么了。”我随意一笑,“管它是青是绿的呢。”
“嘿——”他长叹了一声,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了?”我说,“对我们这老农失望了?”
“大成,要是当年不是为了我,你上了高中大学,现在你可能就是城市里吃皇粮的人了。”他一脸愧色,又提起了那事,“何苦现在太阳底下搬石头呢?真是我害了你啊,这个债我十辈子都还不清。”
“你个狗卵的,怎么又提那猴年马月的狗屁事?陈粮都难吃,你老话重提有什么味头儿?”我瞪了他一眼,“你没听松爷讲,人是有命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天地要你站着死,你就别想躺着活。前几年上岩村出了个县长,全村雀跃,可庆祝的酒肉都还没吃完,没几天那县长就腿一蹬死了。这就是命!什么皇粮不皇粮的,没有谱的事情,咱们这里的糯米饭我就觉得比那什么皇粮好吃多了。”
“你这是安慰话。”他轻轻地摇摇头,好像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
3
“狗卵的,你爱听不听,想钻牛角尖随你去。”他的固执让我有几分不耐烦了,但我压着火气没有发作,“这没有喂饲料的鱼,你是吃过的,比城市里卖的那些好吃多了,价钱是饲料鱼的两三倍呢。现在你不让我吃糯米饭,不让我吃草养的鱼,我活不下去,换个县长我也不当。”
他看了看我,似笑非笑的样子。我一扬手,说:“休息一阵,也不是明天就来大水了。”
我们喝了两盅凉水,就开始抽烟。他吐了两口烟,盯住河面,犹豫了好久才说:“大成,你知道我这腿怎么瘸的?”
“不是工地上摔的?”我装作认真地问,其实我心里早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儿。
“那是骗他们的。”他平静地说,“根本没到什么工地去做过活。”
“那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虽然知道他不是摔断的,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断的。
“被车压断的。”他说的时候浑身不由地颤抖了一下,好像正有一只车轮重重地压过去。
“出车祸了?”我盯住他问。
“不是车祸,是为了救人。”他又回到了平静,就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救人?”我惊讶地看着他,“救什么人?”
他把烟头放进嘴里,又拿了出来,说:“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后到街上去逛,回来的路上看到一辆小轿车失去控制向下冲,但前面有个几个小孩子正在路边玩耍。其他孩子看到了都跑开了,可有一个孩子被吓坏了站那一动不动。我当时就在对面,当然附近不止我一个人,其他人都在喊,可没一个人去救那孩子。我就冲了过去,把孩子抱起来就跑,可焦急的时候滑了一脚,冲下来的车轮正好从我的左脚掌上压了过去,把骨头压得卡卡响,痛得我直喊娘,治好后我就成了这样子。”他把鞋子脱掉,我第一个看到了那个扭曲的脚掌,像一块变形的仙人掌,“狗娘养的,混了半辈子,从城市里就带这么个东西回来。”
“谁给的医药费?”我关心地问。
“那个开车的。”他回答,“他还给了我两千块赔偿。”
“那个孩子的父母没个表示?”我接着问。
“他们给了我三百块钱。”他伸出三个指头。
“才三百?你可救了他们孩子一条命。”我心里愤愤不平地叫了起来。
“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去城里打工的,有几个钱?”他不已为然,“再说了,也不是他们的错。”
“那你为什么骗家里人说是工地上摔的?”我不理解地看着他。
“要是我说了真话,他们不把我当傻瓜?”他嘴里喷出一丝冷笑。
“救人怎么是傻瓜?”我反问。
“你见过我们这里有谁为了救别人把自己的一条腿搭上的吗?这不是傻瓜是什么?”
他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我想他是对的。如果他告诉家里事实,他们可能会指着他的那条瘸腿说:“就为了救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你连命都不要了不是?你以为你的命是自己的?那人是你爹娘兄弟?”他们会把他骂得体无完肤,连祖宗十八代可能都要跳出来骂他不孝。而村里的其他人知道了,也会笑得前翻后仰:“杨家二小子是个癫子。”不仅会笑他本人,还笑他一家子,说他们家的祖坟一定出了问题。人传人,嘴传嘴,这消息可能还会传到隔壁村去,直到藏在群山里的所有村寨都知道了。那时候其他村的人就会在我们九井人的面前眉开眼笑地说,我们村出了个十足的傻子。就算他们指不出名,道不出姓,可他们依旧说得津津有味,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这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杨少平跟我说了腿瘸的真相,好像一下子轻松了好多。他把烟蒂丢进河里,河水立刻把它带走了。但我心里却泛起了另一个疑问,很想知道此后四年他的情况。我问:“那你腿瘸了怎么不回来?”
“回来做什么?”他一脸茫然,“一分钱没往家里寄,倒拖回来了一条瘸腿,粗活重活做不来,早回来早遭骂?还不如给家里多留着一口粮。”
“大伯大妈你哥你嫂也不至于这样吧?怎么都是一家人呢,再说你也不是故意把腿打坏的。”我安慰他。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怎么想?特别是我那嫂嫂,看着我吃白食,她眼里没沙子?我怕受不了那气,所以我就一直没回来——”他若有所思迪抿着嘴,停了一下,“可还是回来了。”
“那你这四年做了什么?你总不会靠着那几块赔偿的钱吃喝吧?”我接着问。
4
“一个没了健全的身体的人,还想靠卖体力吃饭实在不行啊。我一出事就被原来那个厂子赶出来了,最后半个月的工钱都没拿到。”说到这里的时候,他似乎因为愤怒而停顿了一下,“我又找了其他活,可是最后都不如意,不是工钱太少,就是活儿难做。更让我受不了的是,一进去,就没人正儿八经地叫过我的名字,开口闭口一个瘸子。好像你的腿一瘸,连姓甚名谁都改朝换代了,好像你就不是人了,连个畜牲都不如——你看人家城里人,养条长毛狗当儿子,那吃的穿的,我们这些农村去的真的比人家的一条狗都不如——可是,同样是从农村里去的那些人,他还一口一口一个瘸子,一口一口一个残废的,我受不了。所以,我以后就没进过厂子。”
“那你干什么去了?”我一百个不解地看他,“你拿什么过日子来着?”
“怎么过日子?”他的脸上浮出一丝苦笑,“没了做工的地儿,我一直在想办法。手里的那几个钱也一天一天薄了,我想总不能饿死在城里吧,像吴金贵那样连祖坟都进不了。我以前听一个工友说,他的一个老乡捡垃圾每天都能卖到四五十块的,我就动了念头。可去干了才知道,事情没那么容易。捡垃圾也要有秘诀,可我是新手不懂这个。捡垃圾的人可多了,这些人脸皮子厚,比老松树的皮都后,为了一个易拉罐,他能跟着人家屁股走两里路。我哪有那能耐啊?很快我就不干了。我就想了其他办法,我去当了个小厂的门卫。那个门卫也就是做个样子,什么也不用做,一个月五六百块钱。可有个地方睡,也有吃的地方,不至于流落街头饿死。我死撑着做了一年,那个厂子就倒闭了。如果没倒闭,我也会走的。那点钱,在城市里,抽烟都不够。”
我问:“那你到哪里去了?”
他说:“后来我和人家凑合去摆了一阵地摊,开始还可以,两个人分到了一两千块。可有一个事,就是老要做贼一样躲着城管。但那是人家的地盘啊,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还是让人家给逮住了。先放着被没收货物不说,还被带到拘留所关了两天。那是我第一次进那地方,以为再也出不来了,像王秃子那样可就惨了。还好,第二天就出来了。我就像死而复生一样,发誓以后死也不进那地方了。”
我迫不及待地问:“那以后呢?”
他叹了一口气:“出来以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嘛?那个跟我一起摆地摊的,说他有几个朋友在城里做生意,说他可以带我去跟他们合伙干。我问他是不是摆地摊,我可不干这活了。他说,不是摆地摊,可比摆地摊能赚钱。我想该不会是干什么偷摸的事吧。可看他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怎么也觉得不可能。他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生意,却一直在问我干不干。左一个患难兄弟,右一个患难兄弟的,还说什么是我他才叫我入伙,换了别人,下跪求他他也不干。我终于还是被他说动了,说干就干,你这么看得起我,拒绝了就不是人了。这下子他高兴了,连连叫了好多声兄弟。可这一去,你知道干什么的吗?真是怕鬼见坟地,怕狐狸闻着骚,就是干那个的——做贼。”
我万分惊诧地问:“你真去做贼?”
他巴咂了一下嘴巴:“一听说偷东西,我的两条腿就软了。那破事,我可从来没干过。在家里的时候,人家地里的黄瓜我都没摘过一根。头一天我就说我不干。可那跟我摆过地摊的说,兄弟,你可答应了我才带你入伙的,你这出尔反尔的,叫我在其他兄弟面前怎么混?我一口咬定说不干,马上就要走。他说不行,不干也得干一次,不然他不好向兄弟们交代。屋里的其他人也附和说了差不多的话,说什么江湖上混饭吃的讲的就是一个义气,我就想这么走了,可不行,更何况我知道了他们的底细。我当时真后悔跟了他来,这不就是胁迫我当贼吗?可我能怎么办呢?如果当时拒绝,他们非当场把我撕碎不可。我就想了个办法,先答应他们,以后再找机会逃脱。”
我心提到了嗓子眼,问:“你逃脱了没?”
他头埋下去又慢慢抬了起来:“第一次跟他们去干那事,还没出门我的尿意就上来了。我一直以为自己胆子挺大,这时候才发现原来比老鼠的还小——城里的老鼠白天还敢过街呢。我们去了一个偏僻的小卖铺附近,他们叫我留下来放风,因为我的腿脚不灵便。还有那个跟我摆地摊过的也留下来了,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但那个人比我胆子大,他问我是不是害怕。我说有点。他说以后习惯了就不怕了,他说他以前在家里第一次偷人家地里的东西的时候也怕,可久了就觉得跟摘自己地里的东西没两样。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拿过人家东西。他先是不信地笑了笑,然后才说什么都有第一次嘛,第一次搞女人还硬不起来呢。”
“那几人已经开始动手了,也不怕,拿着钢筋撬人家商店的门,跟忘了带钥匙撬自己家门一样干。很快那门就被撬开了,他们把里面的钱拿了个精光,还把一些贵重的货物也抱出来了,而且一点都不慌张,就像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出来一样。可是,才走出门,这时候有一个灯光从另一边过来了,是摩托车的灯光。那几个人拔腿就拼命跑,手里的东西也不要了。我也跟着跑,可两条腿都像煮过的面条,使不上力气。那个摩托车一边追一边喊。接着警车也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还开着警笛,好像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一样。我一边跑,一边就哭起来了,连尿都出来了。要是没有瘸,兴许能跑得快些。可是,这一瘸一拐的,怎么跑?那几个人跑脱了,我却被逮住了。那个店主拿着根胳膊大的棍子要敲我,还好警察拦住了,说打死人不好。所以那怒气腾腾的店主只在我身上踢了两脚解气,要不然我可要被敲得脑瓜都烂了。”
5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水,好像说了这么多话比干体力活还费劲。我没有插话,我知道他的话还没说完。
“后面你也应该知道了的。”他羞愧难当地看了我一眼,“我被带到了派出所,那些警察就像审查汉奸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对我审问。他们叫我说实话,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把知道的都跟他们都说了,从怎么认识摆地摊的一直说到那天晚上,可他们又不信。我当时就要疯了,哭哭啼啼地跪地求饶——嘿,连自己的父母都没跪过呢。他们又问我的脚是怎么瘸的,我说是为了救一个小孩被车碾的。他们说,还没听过小偷还会救人呢。我说我是被骗被逼的,我不是小偷。可谁信?他们都摇头,把脑瓜摇得跟鬼师手里的铃铛似的,说只听过被骗跟男人上床的女人,没听过被骗去当小偷的。我想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当着他们的面就狠狠掴了自己一个耳光。”
“我没想到,刚离开拘留所才几天,自己又进来了。而且这次比上次更加严重,我绝望地哭了。在同一个房里的,听见我哭,就说兄弟不要哭,你没孩子没老婆的,伤心个球。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气,就冲着他吼,老子是被逼的。那人却不为所动一副笑脸说,你冲我吼顶个屁用,哪个偷东西的说自己是小偷?我到城里就没干过正经的活,可我也没跟他们说我是小偷啊。你就忍着点吧,关上十年八载的,不用拼死拼活给人家当奴挣钱,还有吃有穿,病了还有人帮你打针开药,多好的事情。他那样子好像早就盼着坐牢一样。
“我说就是天天给我吃大鱼大肉,喝茅台五粮液,我也不想老死在牢里。那人说,那你不是进来了嘛,想不想都不关你的事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睡个好觉,明天等着给你判刑吧。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就一边哭一边准备睡去了。可哪里睡得着?我是睁着眼睛等到天亮的,好像过了今夜以后就再也没机会睁开眼睛了。
“第二天审判了,我们一群人就像等待挨刀的鸭子站成一排,手脚都被锁着。我们些人之中,有做贼的,有搞传销的,有诈骗的,干什么的都有。有的人一叫到名字就瘫下去了,有的人则什么也不在乎还带着一脸神气的笑,跟小时候被老师点名表扬一样。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也快要倒下去了,不过昨晚同房那个人的话好像起了作用,我坚持地站立着,一声不吭像个哑巴。我被判了一年半。听到那几个字从法官嘴里迸出来,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感觉,又兴奋又害怕。我以为会被判个十年八载,甚至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可是没有那么严重,我心里的确还有些许的希望;可是,转念一想,自己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关进那地方一年半,实在又心痛又后悔。
“到了真正的监狱,那个真是暗无天日,度日如年。好像时间都像牛皮膏一样被煮热拉长了,白天长,黑夜也长。白天等着黑夜到来,黑夜又盼着白天到来。我在牢里常常想到家就哭,虽然知道了只有一年半,可是一想到家我就像被判了死刑,就等着第二天拉去刑场。我很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四年前我离家之前,你叫我不要去了,说只要动脑子肯勤劳在家里同样能挣到钱。你说城市里挣钱也不容易,咱手上没本事,卖的就是一身血汗,不能干一辈子。在牢里,这些话我都一字一句地全想起来了,真是后悔莫及。可有什么用,都太迟了。”
他又停住了,怯怯地扫了我一眼,把那点痛悔锁在了眉宇间。四年前他要走的时候,我的确掏心肝跟他谈了不少话。我是吃够了城里做活的苦,不愿意再去受那窝囊气。在家里上山下地挖田砍柴虽然也累,但没人跟着屁股管你骂你,比城里自由,饿一餐吃一餐。我们一起打工的两年里,他比谁都想家,连做梦都想。我以为他再不去了,可听他说过完年还去,我吃了一惊。如果他当初听我的话,那条腿就不会瘸,也不会闹出那么多故事。
杨少平不停地摇着头,又接着说:“我本来要到冬天才满期的,可在里面没惹什么事,又有积极表现,就提前半年出来了。出来我又去找点活干,挣到几个钱买了身像样的行头,这就回来了。”
说完他长长地松了口气,嘴角现出若隐若现的笑意,好像闷在心里堵塞的东西终于被疏通了。他看了我一眼,又点燃了一支烟,望着天边,旁若无人地抽了起来。
“都是这狗卵的瘸腿害的。”安静中的杨少平骂了一声,“人得有两条好腿,不然这路就走歪了。”
说完他突然举起手边的一块石头。我以为他要砸自己的脚,被吓了一跳,刚想从他手里抢过来,他却将石块向河心投去了,狠狠地骂了几句。静静流淌的河水,像一群被惊吓的鸭子,立刻荡出一片不安的水花。
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到山头上了,红红的一个,像熟透了的柿子,又像腌过的蛋黄。夕阳余晖洒落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间,染出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铺满天边的彩霞,更像一片开在天上的映山红。可是,谁知道这样安详的世界里,曾经发生过多少不安详的故事,又有多少不安详的故事将要发生?我们山里的人的命运就像头顶上的天空,也被群山圈着。这是一种保护,有时候也是一种伤害。
我望着眼下被夕阳染红的静静流淌的河水,正一个浪头跟着一个浪头向山外流去,像是大山里流出的血液,像一群赶路的行人,像流动的目光。再看看杨少平静默的脸庞,犹如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几千年的石头,许多故事都写在上面,却又难以读懂。
我听说杨少平前两天已经从城里打工回来了,还带来了一条瘸腿。村头巷尾人们已经当香饽饽一样议论着这件事,唯独我还没见到他的人。自从出去打工那天算起,这小子,已经有四年没回家过年了,平时一个字也不往家里捎,好像早就忘了山里还有个家,还有生他养他的爹娘。
我们山里把过年过节家人团圆看得比什么都重,有些人到外面闯荡一年,到头来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但还是想方设法借钱甚至一路乞讨赶在年前回来了。回到家里,非但没有遭骂,欠的钱家人还得东凑西凑替还上了。大家都信奉那样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见了平安回来的人,往日的气话怨言,就像见了太阳的晨雾,立刻烟消云散了。我们这里,去城里打工常年不回家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还在坐牢的王秃子,一个是死在外边的吴金贵。他们不回家是情有可原,而他杨少安不回家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他家里人逢年过节也没少叨念他,只是各有各的态度:老父亲骂他忘了祖宗,连畜牲都比不上;哥哥嫂嫂说他心里没个“孝”字,一个人在外面畅快,撂下父母不闻不问;最受罪的是老母亲,逢年过节都少不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向人倾诉对儿子的挂念。儿行千里母牵挂,牵挂的又何止做母亲的呢?
现在,新年早过,年关尚远的时候,杨少平却大张旗鼓地回来了,也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况且还带来了一条瘸腿。
这阵子我正为鱼塘加坝忙死忙活,以防即将到来的雨季。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没来得及去找他讨根烟抽,杨少平却先找上门来了。他来的时候,我正在河里捡石头往岸上抛。这小子,还是和以前一样,远远的就拉开了嗓门。
“大成,你个卵崽,自立门户了?”他一边喊一边朝我走来,一瘸一拐的,“月亮都快上来了,把大叔一个人撂家里,鱼塘当家了不是?”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拍拍手上的泥灰,走上了岸,有些意想不到,“我正愁着没烟抽呢。”
“我家里去找你了,叔说你还在河边。”他一边说一边从胸口的衣兜里往外掏烟盒子,“我问叔河边什么地方。他说鱼塘,我就来了。我听说你承包了这十亩鱼塘。”
“我看这鱼塘荒废着怪可惜的就承包下来了。”我说着已经接过他递来的烟点着了,“你成大老板了,抽中华,一根顶我们老农一天的工钱呢。”
“嘿,剩半条贱命回来已经是祖宗保佑了,还老板呢。”他嘴边抿出一丝苦笑。
“你还记得祖宗呢,我以为你早就换了祖宗呢。”听他嘴里蹦出“祖宗”这两个字,我就犯起了数落他一下的念头。
“你小子就不忘拿我寻开心。”他不愠不怒,拿白眼瞪了我一下,“听说这两年赚了不少,是个人物了你。”
“拿身体血汗当本钱,挣几个酒烟钱。”我说,“说不上赚。”
“对我你还口严,别欺负我初来咋到啊,我可都听说了。”他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乡亲们现今一开口可都先提到你潘大成响当当的大字。”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我打量了一下他的腿,“怎么回事儿?”
他眉头立刻微微皱了起来,现出难看的一脸表情,对着天边深深地吐了一口烟,送出一句:“一言难尽。”
“想不想尝尝没有吃过饲料的鱼?”看他很是难过的样子,我也不好再追问下去。
“不想吃我来找你做什么?”就像瞬息万变的天,他立刻又浮起了满脸奸邪的笑意,“网两条来尝尝鲜,说真的,几年没吃过咱们这里的鱼了。”
我网了两条斧头板大小的鲤鱼,问他:“够了没有?”
他笑了笑说:“我又不是饥民,你还真当我是讨饭的?”
晚上我把对面的蒋松爷也叫来了,加上我爸,四个人也没把两条鱼吃完,倒把家里剩的半瓮米酒喝个精光。杨少平向来不胜酒力,几年不见,其他的地方好像都变了,唯独这项没一点变化。站起来他已经摇摇欲坠了,嘴里含混不清地骂着什么。出门的时候,他坚持说自己没事,但两位老人还是不放心他一个人走路,叫我把他送回家。我把他送进门后,才折回了鱼塘的小屋。
外面是洗过一样清澈的月光,洒落在四周静谧的田野上。和月光一样清澈的,是我没有一点睡意的眼睛。我走出了小屋,坐在坝上抽起了烟来。远处的秧苗正在抽长,在晚风的吹拂中翻滚着,阵阵草香沁人心脾。但让我无法入睡的,不是月光,也不是草香,而是杨少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那只跛脚。
2
我和杨少平同一年出生一起长大的,但并非从小就是好朋友。和其他孩子一样,那时候他也从心里瞧不起我,一样骂我是没妈的野孩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初中。初中毕业前夕,杨少平和镇上的学生发生了矛盾,被几个人拿着棍棒围攻,在场的没一个肯出手相救,就是平日称兄道弟的那帮人这时候也做了缩头乌龟远而避之。眼看那帮人的乱棍就要劈头盖脸落下的时候,我冲进食堂厨房抓了一把菜刀冲了过去。见到我手里明晃晃的菜刀,那帮镇上学生退却了。杨少平得救了,但我和他不得不离开了学校。从此,他把我当成了救命恩人,欠了我的人情。每次提起这件事,他都觉得很愧疚,说他毁了我的前程。因为那时候我在班上的成绩名列前茅,老师觉得我有望考得了高中,将来可能还上大学。但为了他,一切都成了泡影。我告诉他,初中三年已经让我家里不堪重负了,我从来没指望上什么高中,更别说大学了。但他还是不停地摇着头,唉声叹气地重复一句话:“你救了我,我却害了你。”
我告诉他,相比于上什么高中什么大学,朋友对我来说更重要。那些东西太遥远了。我从小到大没有过一个朋友,无心树敌,把我当敌人的却一大堆。他很负疚以前对我那样坏,发誓以后一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我。为了让我相信他的话,他把自己的指头咬坡,在村外的石头上写下了“兄弟”两个血字。虽然那两个字早被风雨吹刷干净了,但每次路过的时候,我总情不自禁地停下来。想起夕阳下两个少年信誓旦旦称兄道弟的样子,心里就像装满了春风。
从学校出来后,我们又在家里度过了空虚的两年,然后结伴下广东打工去了。我去了两年,受够了城里的气,就不再去了。而他坚持只身南下,誓言闯出一片天来。谁想到四年后再见,他的豪言壮语已经化作一道抹不去的伤疤。
杨少平瘸腿的事,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揣摩着答案。有人说,他是跟人打架被打断的,有人说他是出了车祸,有人说他是欠赌债被人敲断的……人们凭着自己力所能及的想象,各衷一是。而他本人在家人的追问下,说是在工地上摔断的。我既不苟同人们毫无根据的猜测,也不相信他跟家人说了实话,但我也没打算问他。既然他不说,就一定有他的原因。被人逼迫说出自己不愿意透露的隐情,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我很久以前就尝试过了。一个人,没有经历过你经历过的那种痛苦,就算他口口声声对你说他能理解,也不能体味到万分之一。所以历来我都没有刨根问底的习惯,因为我也一直逃避着被人刨根问底的目光。
杨少平闲在家里也不知道干什么,就来鱼塘帮我的活。说实在的,他垒石头的水平比我高,可能这有遗传因素。他祖上曾是有名的石匝,他的爸爸和哥哥都是垒石头的好手。我们村子里谁家起新房开房坪,都喜欢请他们父子俩。
“想不到一回来就成名人了。”杨少平几分无奈伴着几分自嘲地说,“可惜巴掌大的地方,要在城市里,就该上报上电视了。”
“出名是好事啊,有人拿钱还买不来呢。”我跟他开玩笑。
“人怕出名猪怕壮,吃完说不完啊。”他先叹着气,旋即嘴边却露出了满不在乎的笑意,“就让他们说去吧,那嘴巴闲着也是闲着,*不撒尿,还留着当大炮?封闭了几百年,也该松松了。咱们这地方的山多得跟城里的房子一样,活了一辈子就看到个巴掌大的天,还能指望怎么样?”
“听你这么一说,到城市里逛了几年,回来还真瞧不起咱们这山里人啰?”我半认真半玩笑,“先前你爸说你忘了祖宗我还替你不平,现在看来活该。”
“瞧不起我还回来个卵?”他不焦不躁地笑了起来,“说句实在话,想来想去还是咱这里的人好,穷是穷了点,可活得自在,空气都新鲜,不像城市里。书本上说的‘青山绿水’指的就是咱这地方,你说是不是?”
“我可不记得书上说什么了。”我随意一笑,“管它是青是绿的呢。”
“嘿——”他长叹了一声,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了?”我说,“对我们这老农失望了?”
“大成,要是当年不是为了我,你上了高中大学,现在你可能就是城市里吃皇粮的人了。”他一脸愧色,又提起了那事,“何苦现在太阳底下搬石头呢?真是我害了你啊,这个债我十辈子都还不清。”
“你个狗卵的,怎么又提那猴年马月的狗屁事?陈粮都难吃,你老话重提有什么味头儿?”我瞪了他一眼,“你没听松爷讲,人是有命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天地要你站着死,你就别想躺着活。前几年上岩村出了个县长,全村雀跃,可庆祝的酒肉都还没吃完,没几天那县长就腿一蹬死了。这就是命!什么皇粮不皇粮的,没有谱的事情,咱们这里的糯米饭我就觉得比那什么皇粮好吃多了。”
“你这是安慰话。”他轻轻地摇摇头,好像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
3
“狗卵的,你爱听不听,想钻牛角尖随你去。”他的固执让我有几分不耐烦了,但我压着火气没有发作,“这没有喂饲料的鱼,你是吃过的,比城市里卖的那些好吃多了,价钱是饲料鱼的两三倍呢。现在你不让我吃糯米饭,不让我吃草养的鱼,我活不下去,换个县长我也不当。”
他看了看我,似笑非笑的样子。我一扬手,说:“休息一阵,也不是明天就来大水了。”
我们喝了两盅凉水,就开始抽烟。他吐了两口烟,盯住河面,犹豫了好久才说:“大成,你知道我这腿怎么瘸的?”
“不是工地上摔的?”我装作认真地问,其实我心里早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儿。
“那是骗他们的。”他平静地说,“根本没到什么工地去做过活。”
“那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虽然知道他不是摔断的,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断的。
“被车压断的。”他说的时候浑身不由地颤抖了一下,好像正有一只车轮重重地压过去。
“出车祸了?”我盯住他问。
“不是车祸,是为了救人。”他又回到了平静,就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救人?”我惊讶地看着他,“救什么人?”
他把烟头放进嘴里,又拿了出来,说:“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后到街上去逛,回来的路上看到一辆小轿车失去控制向下冲,但前面有个几个小孩子正在路边玩耍。其他孩子看到了都跑开了,可有一个孩子被吓坏了站那一动不动。我当时就在对面,当然附近不止我一个人,其他人都在喊,可没一个人去救那孩子。我就冲了过去,把孩子抱起来就跑,可焦急的时候滑了一脚,冲下来的车轮正好从我的左脚掌上压了过去,把骨头压得卡卡响,痛得我直喊娘,治好后我就成了这样子。”他把鞋子脱掉,我第一个看到了那个扭曲的脚掌,像一块变形的仙人掌,“狗娘养的,混了半辈子,从城市里就带这么个东西回来。”
“谁给的医药费?”我关心地问。
“那个开车的。”他回答,“他还给了我两千块赔偿。”
“那个孩子的父母没个表示?”我接着问。
“他们给了我三百块钱。”他伸出三个指头。
“才三百?你可救了他们孩子一条命。”我心里愤愤不平地叫了起来。
“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去城里打工的,有几个钱?”他不已为然,“再说了,也不是他们的错。”
“那你为什么骗家里人说是工地上摔的?”我不理解地看着他。
“要是我说了真话,他们不把我当傻瓜?”他嘴里喷出一丝冷笑。
“救人怎么是傻瓜?”我反问。
“你见过我们这里有谁为了救别人把自己的一条腿搭上的吗?这不是傻瓜是什么?”
他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我想他是对的。如果他告诉家里事实,他们可能会指着他的那条瘸腿说:“就为了救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你连命都不要了不是?你以为你的命是自己的?那人是你爹娘兄弟?”他们会把他骂得体无完肤,连祖宗十八代可能都要跳出来骂他不孝。而村里的其他人知道了,也会笑得前翻后仰:“杨家二小子是个癫子。”不仅会笑他本人,还笑他一家子,说他们家的祖坟一定出了问题。人传人,嘴传嘴,这消息可能还会传到隔壁村去,直到藏在群山里的所有村寨都知道了。那时候其他村的人就会在我们九井人的面前眉开眼笑地说,我们村出了个十足的傻子。就算他们指不出名,道不出姓,可他们依旧说得津津有味,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这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杨少平跟我说了腿瘸的真相,好像一下子轻松了好多。他把烟蒂丢进河里,河水立刻把它带走了。但我心里却泛起了另一个疑问,很想知道此后四年他的情况。我问:“那你腿瘸了怎么不回来?”
“回来做什么?”他一脸茫然,“一分钱没往家里寄,倒拖回来了一条瘸腿,粗活重活做不来,早回来早遭骂?还不如给家里多留着一口粮。”
“大伯大妈你哥你嫂也不至于这样吧?怎么都是一家人呢,再说你也不是故意把腿打坏的。”我安慰他。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怎么想?特别是我那嫂嫂,看着我吃白食,她眼里没沙子?我怕受不了那气,所以我就一直没回来——”他若有所思迪抿着嘴,停了一下,“可还是回来了。”
“那你这四年做了什么?你总不会靠着那几块赔偿的钱吃喝吧?”我接着问。
4
“一个没了健全的身体的人,还想靠卖体力吃饭实在不行啊。我一出事就被原来那个厂子赶出来了,最后半个月的工钱都没拿到。”说到这里的时候,他似乎因为愤怒而停顿了一下,“我又找了其他活,可是最后都不如意,不是工钱太少,就是活儿难做。更让我受不了的是,一进去,就没人正儿八经地叫过我的名字,开口闭口一个瘸子。好像你的腿一瘸,连姓甚名谁都改朝换代了,好像你就不是人了,连个畜牲都不如——你看人家城里人,养条长毛狗当儿子,那吃的穿的,我们这些农村去的真的比人家的一条狗都不如——可是,同样是从农村里去的那些人,他还一口一口一个瘸子,一口一口一个残废的,我受不了。所以,我以后就没进过厂子。”
“那你干什么去了?”我一百个不解地看他,“你拿什么过日子来着?”
“怎么过日子?”他的脸上浮出一丝苦笑,“没了做工的地儿,我一直在想办法。手里的那几个钱也一天一天薄了,我想总不能饿死在城里吧,像吴金贵那样连祖坟都进不了。我以前听一个工友说,他的一个老乡捡垃圾每天都能卖到四五十块的,我就动了念头。可去干了才知道,事情没那么容易。捡垃圾也要有秘诀,可我是新手不懂这个。捡垃圾的人可多了,这些人脸皮子厚,比老松树的皮都后,为了一个易拉罐,他能跟着人家屁股走两里路。我哪有那能耐啊?很快我就不干了。我就想了其他办法,我去当了个小厂的门卫。那个门卫也就是做个样子,什么也不用做,一个月五六百块钱。可有个地方睡,也有吃的地方,不至于流落街头饿死。我死撑着做了一年,那个厂子就倒闭了。如果没倒闭,我也会走的。那点钱,在城市里,抽烟都不够。”
我问:“那你到哪里去了?”
他说:“后来我和人家凑合去摆了一阵地摊,开始还可以,两个人分到了一两千块。可有一个事,就是老要做贼一样躲着城管。但那是人家的地盘啊,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还是让人家给逮住了。先放着被没收货物不说,还被带到拘留所关了两天。那是我第一次进那地方,以为再也出不来了,像王秃子那样可就惨了。还好,第二天就出来了。我就像死而复生一样,发誓以后死也不进那地方了。”
我迫不及待地问:“那以后呢?”
他叹了一口气:“出来以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嘛?那个跟我一起摆地摊的,说他有几个朋友在城里做生意,说他可以带我去跟他们合伙干。我问他是不是摆地摊,我可不干这活了。他说,不是摆地摊,可比摆地摊能赚钱。我想该不会是干什么偷摸的事吧。可看他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怎么也觉得不可能。他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生意,却一直在问我干不干。左一个患难兄弟,右一个患难兄弟的,还说什么是我他才叫我入伙,换了别人,下跪求他他也不干。我终于还是被他说动了,说干就干,你这么看得起我,拒绝了就不是人了。这下子他高兴了,连连叫了好多声兄弟。可这一去,你知道干什么的吗?真是怕鬼见坟地,怕狐狸闻着骚,就是干那个的——做贼。”
我万分惊诧地问:“你真去做贼?”
他巴咂了一下嘴巴:“一听说偷东西,我的两条腿就软了。那破事,我可从来没干过。在家里的时候,人家地里的黄瓜我都没摘过一根。头一天我就说我不干。可那跟我摆过地摊的说,兄弟,你可答应了我才带你入伙的,你这出尔反尔的,叫我在其他兄弟面前怎么混?我一口咬定说不干,马上就要走。他说不行,不干也得干一次,不然他不好向兄弟们交代。屋里的其他人也附和说了差不多的话,说什么江湖上混饭吃的讲的就是一个义气,我就想这么走了,可不行,更何况我知道了他们的底细。我当时真后悔跟了他来,这不就是胁迫我当贼吗?可我能怎么办呢?如果当时拒绝,他们非当场把我撕碎不可。我就想了个办法,先答应他们,以后再找机会逃脱。”
我心提到了嗓子眼,问:“你逃脱了没?”
他头埋下去又慢慢抬了起来:“第一次跟他们去干那事,还没出门我的尿意就上来了。我一直以为自己胆子挺大,这时候才发现原来比老鼠的还小——城里的老鼠白天还敢过街呢。我们去了一个偏僻的小卖铺附近,他们叫我留下来放风,因为我的腿脚不灵便。还有那个跟我摆地摊过的也留下来了,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但那个人比我胆子大,他问我是不是害怕。我说有点。他说以后习惯了就不怕了,他说他以前在家里第一次偷人家地里的东西的时候也怕,可久了就觉得跟摘自己地里的东西没两样。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拿过人家东西。他先是不信地笑了笑,然后才说什么都有第一次嘛,第一次搞女人还硬不起来呢。”
“那几人已经开始动手了,也不怕,拿着钢筋撬人家商店的门,跟忘了带钥匙撬自己家门一样干。很快那门就被撬开了,他们把里面的钱拿了个精光,还把一些贵重的货物也抱出来了,而且一点都不慌张,就像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出来一样。可是,才走出门,这时候有一个灯光从另一边过来了,是摩托车的灯光。那几个人拔腿就拼命跑,手里的东西也不要了。我也跟着跑,可两条腿都像煮过的面条,使不上力气。那个摩托车一边追一边喊。接着警车也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还开着警笛,好像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一样。我一边跑,一边就哭起来了,连尿都出来了。要是没有瘸,兴许能跑得快些。可是,这一瘸一拐的,怎么跑?那几个人跑脱了,我却被逮住了。那个店主拿着根胳膊大的棍子要敲我,还好警察拦住了,说打死人不好。所以那怒气腾腾的店主只在我身上踢了两脚解气,要不然我可要被敲得脑瓜都烂了。”
5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水,好像说了这么多话比干体力活还费劲。我没有插话,我知道他的话还没说完。
“后面你也应该知道了的。”他羞愧难当地看了我一眼,“我被带到了派出所,那些警察就像审查汉奸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对我审问。他们叫我说实话,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把知道的都跟他们都说了,从怎么认识摆地摊的一直说到那天晚上,可他们又不信。我当时就要疯了,哭哭啼啼地跪地求饶——嘿,连自己的父母都没跪过呢。他们又问我的脚是怎么瘸的,我说是为了救一个小孩被车碾的。他们说,还没听过小偷还会救人呢。我说我是被骗被逼的,我不是小偷。可谁信?他们都摇头,把脑瓜摇得跟鬼师手里的铃铛似的,说只听过被骗跟男人上床的女人,没听过被骗去当小偷的。我想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当着他们的面就狠狠掴了自己一个耳光。”
“我没想到,刚离开拘留所才几天,自己又进来了。而且这次比上次更加严重,我绝望地哭了。在同一个房里的,听见我哭,就说兄弟不要哭,你没孩子没老婆的,伤心个球。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气,就冲着他吼,老子是被逼的。那人却不为所动一副笑脸说,你冲我吼顶个屁用,哪个偷东西的说自己是小偷?我到城里就没干过正经的活,可我也没跟他们说我是小偷啊。你就忍着点吧,关上十年八载的,不用拼死拼活给人家当奴挣钱,还有吃有穿,病了还有人帮你打针开药,多好的事情。他那样子好像早就盼着坐牢一样。
“我说就是天天给我吃大鱼大肉,喝茅台五粮液,我也不想老死在牢里。那人说,那你不是进来了嘛,想不想都不关你的事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睡个好觉,明天等着给你判刑吧。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就一边哭一边准备睡去了。可哪里睡得着?我是睁着眼睛等到天亮的,好像过了今夜以后就再也没机会睁开眼睛了。
“第二天审判了,我们一群人就像等待挨刀的鸭子站成一排,手脚都被锁着。我们些人之中,有做贼的,有搞传销的,有诈骗的,干什么的都有。有的人一叫到名字就瘫下去了,有的人则什么也不在乎还带着一脸神气的笑,跟小时候被老师点名表扬一样。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也快要倒下去了,不过昨晚同房那个人的话好像起了作用,我坚持地站立着,一声不吭像个哑巴。我被判了一年半。听到那几个字从法官嘴里迸出来,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感觉,又兴奋又害怕。我以为会被判个十年八载,甚至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可是没有那么严重,我心里的确还有些许的希望;可是,转念一想,自己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关进那地方一年半,实在又心痛又后悔。
“到了真正的监狱,那个真是暗无天日,度日如年。好像时间都像牛皮膏一样被煮热拉长了,白天长,黑夜也长。白天等着黑夜到来,黑夜又盼着白天到来。我在牢里常常想到家就哭,虽然知道了只有一年半,可是一想到家我就像被判了死刑,就等着第二天拉去刑场。我很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四年前我离家之前,你叫我不要去了,说只要动脑子肯勤劳在家里同样能挣到钱。你说城市里挣钱也不容易,咱手上没本事,卖的就是一身血汗,不能干一辈子。在牢里,这些话我都一字一句地全想起来了,真是后悔莫及。可有什么用,都太迟了。”
他又停住了,怯怯地扫了我一眼,把那点痛悔锁在了眉宇间。四年前他要走的时候,我的确掏心肝跟他谈了不少话。我是吃够了城里做活的苦,不愿意再去受那窝囊气。在家里上山下地挖田砍柴虽然也累,但没人跟着屁股管你骂你,比城里自由,饿一餐吃一餐。我们一起打工的两年里,他比谁都想家,连做梦都想。我以为他再不去了,可听他说过完年还去,我吃了一惊。如果他当初听我的话,那条腿就不会瘸,也不会闹出那么多故事。
杨少平不停地摇着头,又接着说:“我本来要到冬天才满期的,可在里面没惹什么事,又有积极表现,就提前半年出来了。出来我又去找点活干,挣到几个钱买了身像样的行头,这就回来了。”
说完他长长地松了口气,嘴角现出若隐若现的笑意,好像闷在心里堵塞的东西终于被疏通了。他看了我一眼,又点燃了一支烟,望着天边,旁若无人地抽了起来。
“都是这狗卵的瘸腿害的。”安静中的杨少平骂了一声,“人得有两条好腿,不然这路就走歪了。”
说完他突然举起手边的一块石头。我以为他要砸自己的脚,被吓了一跳,刚想从他手里抢过来,他却将石块向河心投去了,狠狠地骂了几句。静静流淌的河水,像一群被惊吓的鸭子,立刻荡出一片不安的水花。
这时候太阳已经落到山头上了,红红的一个,像熟透了的柿子,又像腌过的蛋黄。夕阳余晖洒落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间,染出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铺满天边的彩霞,更像一片开在天上的映山红。可是,谁知道这样安详的世界里,曾经发生过多少不安详的故事,又有多少不安详的故事将要发生?我们山里的人的命运就像头顶上的天空,也被群山圈着。这是一种保护,有时候也是一种伤害。
我望着眼下被夕阳染红的静静流淌的河水,正一个浪头跟着一个浪头向山外流去,像是大山里流出的血液,像一群赶路的行人,像流动的目光。再看看杨少平静默的脸庞,犹如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几千年的石头,许多故事都写在上面,却又难以读懂。
PS:因为时间关系,更多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广西最大的原创文学社区社区“红豆社区”阅览。《山里的男人》已经被推荐到红豆社区首页,欢迎大家斧正批评:【长篇连载】山里的男人http://hongdou.gxnews.com.cn/viewthread-588184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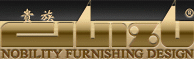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